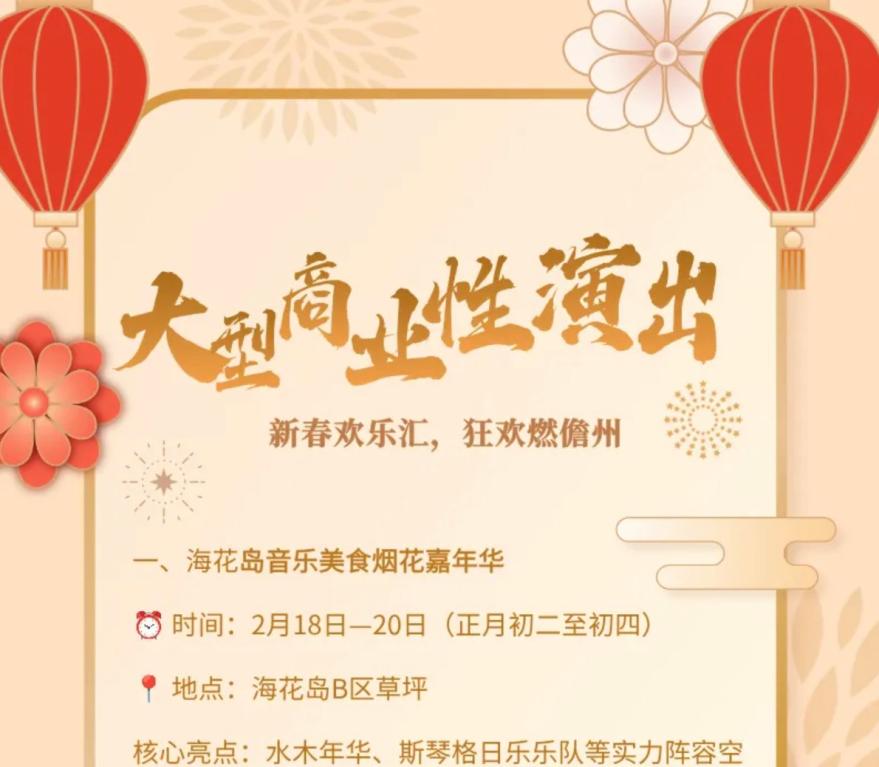【编者按】
200年前,广东番禺一个书香门第诞生一位才华出众的奇女子许小韫,后来嫁给海南定安高林村探花张岳崧的长孙为媳,丈夫去世后,她服侍寡居的婆婆吴氏20余年,直到吴氏离世,她便绝食殉世。
许小韫新婚时命名的居室“柏香山馆”即将得到修缮,在那里,她创作了100多首诗词,留下了她对生活的观感、对生命的思索,字里行间,写满悲欢离合。
在定安高林村张岳崧故居旁,柏香山馆遗址默然伫立。残垣之上荒草丛生,行走其间,脚下砖瓦似有低徊的悲鸣。这座小小的山馆,曾是才女许小韫的栖身之所,也静静见证了她后半生的悲欢起落。
步入庭院,可见一间简朴小屋。相传许小韫曾居于此,侍奉长辈起居。
风过庭阶,草木低语,一段沉寂近两百年的往事,随之缓缓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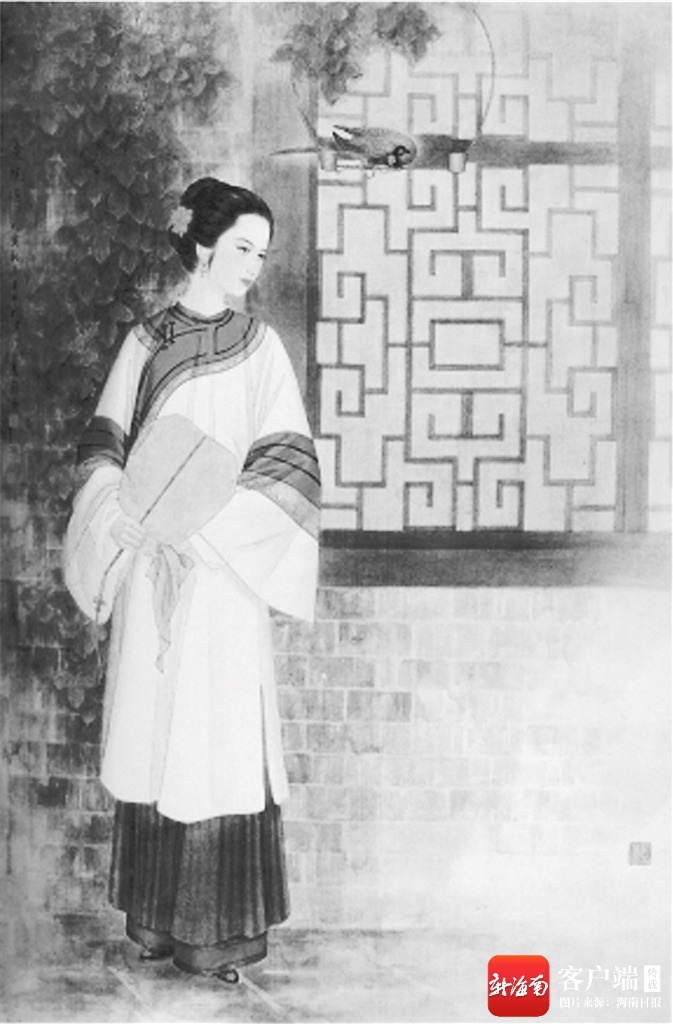
许小韫画像。资料图
番禺才女琼州姻缘
清代道光五年(1825年),许小韫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就展现出过人天赋。清代光绪《定安县志》称她“工诗善画,能文精绣”,其弟许其光后来考中榜眼,可见家族文化底蕴之深厚。
20岁那年,她嫁给了海南探花张岳崧的长孙张熊光。传说初次见面,许小韫出一联“妙少女,原心愿配己酉郎”,张熊光即刻回应“张长弓,寸身射破石皮鼓”。
新婚燕尔,两人情投意合,琴瑟和鸣。她将住屋取名“柏香山馆”,常与丈夫一同吟诗作画,陪伴他研读经史。这段时光的美好,流淌在她的《柏香山馆即事》中:“绿阴庭院午风凉,阶砌名花各吐芳。植就两株青翠柏,他年留得凛风霜。”“小池微雨绉清波,荡漾秋风卷碧荷。独倚栏杆无一事,闲将蚱蜢饲巴哥。”
初到海南,她对本地风土人情抱有好奇,在《寒食有感》中写道:“年年寒食写新诗,细雨东风忆旧时。谁谓禁烟厨灶里,小堂日暮尚频炊。”北方寒食禁火,而海南无此风俗,这份灵秀通透,让她感悟并融入当地的文化脉搏。
“盈盈金阙彩云开,乍见冰轮焕镜台。神女无心遗珮去,鲛人有意送珠来。描形拟作班姬扇,对影应浮太白杯。会遇良宵诗兴好,愿教铜漏且停催。”她在《柏香山馆看月·圆月》中,通过“神女”“鲛人”等仙逸意象,展现出高雅超俗的审美人格和文人面对月亮时永恒的精神探索。

许小韫与婆婆吴氏住过的房屋及庭院。雷英杰摄
琴断柏香代夫尽孝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婚后第七年,张熊光因染疫病逝,唯一的女儿也夭折。27岁的许小韫悲痛欲绝,想要追随丈夫而去。
但家中还有一位命运更为凄惨的婆婆吴氏——同样是年轻时丧夫,老年又失去儿子,孤寡无依。许小韫强忍悲痛,替夫行孝。据《定安县志》记载:“(小韫)所以不殉者,以孀姑(指婆婆吴氏)在堂耳,事姑极柔顺。姑病笃,宵间无人见知之时,出庭焚香祷天求愈。”
许小韫守寡的日子里,诗词成为她的情绪出口。她先后写下了11首悼亡诗,悲咽哀婉,如唳鹤啼鹃,字字句句都是刻骨的思念,如《悼张锡卿夫》:“不道文章与命乖,香泥玉树恨同埋。伤心试睹君遗札,寂寞琴书空小斋。从此见君空有梦,九原无路慰相思……”“自君之逝矣,懒上旧妆楼。蠹蚀琴书冷,萤飞枕簟秋。”“每睹箧中物,空悲泉下人。”
她睹物思人,“偶然触目亦伤神”,但她强忍悲痛,在婆婆面前和颜悦色,“犹将宽语慰慈亲”(《悼张锡卿夫》,锡卿是张熊光的字)。
她的诗风在婉约哀戚之中,又自带风骨和克制。在《自劝》诗中自我宽慰:“莫怨霜鸾命早孤,神仙富贵岂同途?由来伯道原无子,何必罗敷定有夫。”也在《慰胡英花魏淑媛二闺秀》中勉励同样青年丧偶的闺蜜:“养就岁寒松柏质,愁缘却尽了前因。”这份在苦难中升华出的豁达与通透,或许是她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
在漫长的守寡岁月里,许小韫通过与胡英花、魏淑媛二位姐妹唱和诗词,排解孤寂。而婆婆吴氏作为家族的管理者,理解并支持儿媳的文学创作。
族谱记载,吴氏是探花张岳崧的长子张钟銮之妻,是原任浙江宁海知州会同吴嗣湖的孙女,也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都说长嫂如母,张钟銮二十七岁病逝后,吴氏承担起侍奉公婆、教育子侄的责任。
《定安县志》称其“上事下养,茹冰饮蘗者四十年。不惟有贞正之德,且兼多干济之才,诚女中丈夫也。提携训迪诸幼叔长成,钟璘等亦孝友,恂恂事之如母,罔敢稍忽。以巾帼妇人而有士君子之识焉,卓然可为闺阃中遭事势之艰者作仪型也。里党钦其懿行,例合旌表,咸丰七年,貤封恭人”。张岳崧次子张钟彦、四子张钟琇后来能先后考中进士和举人,有吴氏的一份功劳。
这种文化上的门当户对,使得两人有着更多的精神共鸣。

本文作者(右)在高林村采访探花张岳崧后人。雷英杰摄
教育薪火才情传承
许小韫的才情因教育贡献而更加璀璨。探花第五代孙张运恩老人告诉我,许小韫的婆婆曾劝她:你这么有才华的人,要教我们张家的后代。于是,她开始在高林学馆担任女先生,教育张家子弟。“在她的教导下,高林张氏出了不少举人和贡生。”
探花第七代孙媳刘碧女士说:“当时周边村庄的孩子,都来这里上学,这里就是一所学校。”
许小韫的生命轨迹印证了,真正的才情既能书写个人的悲欢,也能照亮一个家族、一方水土的文化前程。她不仅是清代海南一位杰出的女性诗人,更是一位点燃文明薪火的教育者。在清代女性教育机会尚且有限的环境中,她的教学实践显得尤为珍贵,更使得文化的血脉在海南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探花第七代孙媳刘碧女士表示:“许小韫照顾婆婆,孝顺婆婆,如今我们也要传承我们祖宗的家文化。”这句话让人看到,许小韫的精神依然在高林村传承。
柏树凛霜生死相随
《定安县志》记载了她最后的时光:“不幸姑亡,痛哭几绝。诚慎殡毕,慨然曰:‘吾可以死矣!’遂绝食数日殉。事皆一月内。”
1869年,守寡40余年的婆婆吴氏病逝。送婆婆入殓时,许小韫浑身缟素,亲自为婆婆擦身更换素衣。将婆婆安葬后,44岁的她平静地说:“吾可以死矣!”随后绝食数日,也随婆婆而去。
这在当时当地,许小韫的行为既是对丈夫的追随,也是对婆婆的最终守候,将其性格中的刚烈、忠贞与决绝展现到了极致。
许小韫死后,与婆婆吴氏合葬在一处。在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仕梅头村,两座一般高的清代古墓石碑紧紧相偎,恰似婆媳二人在世时相互扶持的模样。
她早年的诗句“植就两株苍翠柏,他年留得凛风霜”,仿佛成了生命的预言。她如柏树般坚韧地度过了将近20年的寡居生活,最终以惊世之举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许小韫的三叔、探花张岳崧的三子张钟璘怜惜她的才华,将其零散的134首诗稿整理成《柏香山馆诗卷》并刊印。他在《题小韫柏香馆诗卷跋》中写道:“谁将五色笔,收拾在妆台?云锦天孙织,琼花帝女栽。愁因怀旧结,心为悼亡灰。读罢一掩卷,问天何妒才!”
可惜这部诗集最终失传,仅剩县志上辑录的22首,令人惋惜。
柏香山馆即将修复,期待恢复当年树影摇曳、翰墨书香的模样。
历史的长卷里,有李清照这般鲜活的奇女子,也有许小韫这样决绝的才女。她们用诗词或事迹在史书上留下或重或轻的一笔,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
恰如许小韫《柏香山馆看月·问月》所感怀:“流光千古照人间,多少忧劳与乐闲。为问前身曾识否,只缘何事谪尘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