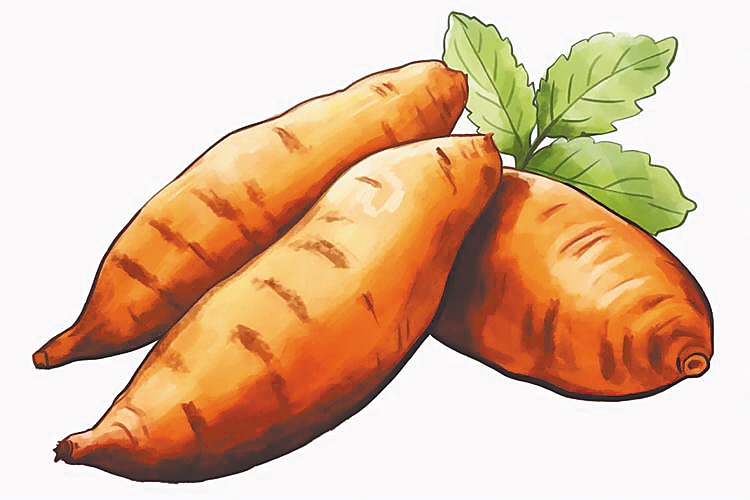在澄迈县的古代八景之中,其中之一为“通潮飞阁”,历代多有官员和文人墨客吟咏,它便是通潮阁,遗址在今天的老城糖厂内。顾名思义,老城即澄迈县的老县城(古称县治)。澄迈县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迁至金江,旧的县城便被唤作“老城”。县治迁徙的原因是1891年知县李德重已在“金江市”(今金江镇)肇建行署,1895年续建的“金江行署”竣工后,时任知县薛贺图便迁往新的衙署。
通潮阁,原名通明阁,位于老城镇原县治西门外,因建在通潮驿所在地而得名。驿站是我国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据《琼崖古驿道》的作者、海南文史专家何以端先生考证,包括通潮驿在内,宋代海南岛的环岛驿全线贯通,通潮阁至晚在北宋时期便已出现,这从苏东坡的通潮阁诗和相关诗文可以得到佐证;通潮驿或通潮阁也有可能出现在隋代或更早的朝代,但由于没有史料证据,因此不能妄下定论。
古代的驿道上设有铺舍和驿站,驿站投资和运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铺舍则只需两三名铺兵、两三间草房即可。

通潮阁附近里桥一带的景观。元博摄
“铺舍一般每十里设一个,譬如明代时期,从府城的琼台驿府门总铺向西出发,第一个铺设为二水铺,旧址在今天的头铺村,再经过业里铺(业里村)、五原铺(富教村)、石山铺(北铺村)、七里铺、县门铺后,便来到海南岛西线的第一个驿站——通潮驿。”何以端说,“依明初规制,出于依托大邑的需要,两个驿站的路程在60里至80里之间,大致按一天的路程设置一座,而且尽可能靠近人口较多的居民点,如县治(县城)等。按当年的路况,步行5公里(一铺的路程)需要2小时计算,走完琼台驿与通潮驿之间6个铺舍的路程,刚好是一天的时间,如果早上6点从府城出发,在晚上6点可到达老城。当然,程距长的,赶路就免不了起早摸黑,程距短的就可以松弛些,譬如府城和老城之间的驿路就属于较短的。”
今天,上了年纪的海南老人尤其是七旬以上的,口头上仍以“铺”作为单位来描述距离,比如会把大约2.5公里的路程,称为“半铺路”。
澄迈县史志办原主任孙中积先生考据文献资料时发现,南宋被贬来琼的抗金名臣李光,曾以柳体书誊写苏东坡的通潮阁诗,当时的县令请人刻在两块石碑上,立于阁内,碑刻各有1米宽、2米高、0.16米厚。
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澄迈知县刘时敏在境内设通潮、西峰二驿。
据光绪《澄迈县志》记载:在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年)之前,澄迈县治并无城池,是年广东按察使巡督边务时,才行文让澄迈典史李黎生创筑土城,周围百丈,然而年岁一久便崩坏了;成化元年(1465年),由于海寇侵扰,沿海地区警报连连,澄迈主簿杨正重筑土墙二里许;成化二十年(1484年),知县韦裘带领民众采伐石块,烧制砖头,“砌筑周围五百八十余丈”,于弘治三年(1490年)告成,使得澄迈县城“西南沿江,东北凿隍,上设警铺,下通水关,三门各设城楼,北建望海楼。佥事李珊碑记。按三门:东曰‘迎恩’,西曰‘通潮’,南曰‘归仁’”。
明代的通潮驿、通潮阁就在澄迈县城西门(通潮门)外,弘治十七年(1504年),广东副使王檵巡察琼州时,发现通潮驿靠近县治(县城),没有必要设置,于是向朝廷奏请革除,得到许可。此后,通潮驿的“驿廨基址”便被营兵占据,当作驻军场所。
正德年间,澄迈知县卢晖将通潮驿、通潮阁建为“公馆”,类似于今天的招待所。
到了嘉靖年间,知县唐启宾重修通潮阁,年久失修后又再次倒塌。
通潮阁大致在清代康熙元年(1662年)前后一度被毁,南宋时期刻录苏轼通潮阁诗的碑记于是不知去向。
道光十五年(1835年),澄迈县教谕兼训导李梓瑶首倡士绅捐建通潮阁于关帝庙左侧,并为之作记和题篆碑额。阁有二层,高三丈,其上祭祀苏文忠公(苏东坡),广东学使李星沅为之题写了对联。
李梓瑶的《通潮飞阁碑》碑刻和一尊须弥座壶门石像于2003年9月在通潮阁遗址附近的山坡上被发现。2024年初,在海南省博物馆的“苏轼主题文物展”上,展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通潮飞阁碑》的拓片。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标,通潮阁在航海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元代《岛夷志略》的记载称,商船“望通潮阁飞檐为向”。估计元明时期,通潮阁拥有恢宏的气势和显著的高度,所以能够成为航海者的方向标。相传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也以通潮阁为出海南洋面的最后一个陆标。
今天,站在通潮阁遗址上北望琼州海峡,潮起潮落间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建遗迹,不仅承载着海南岛的文化记忆,更见证着中华文明向海而生的开拓精神。在这里,但愿历史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永远跳动的文化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