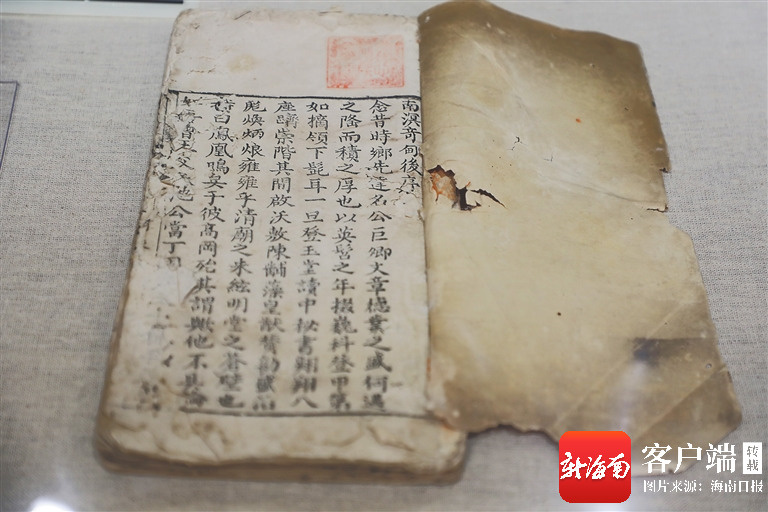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东坡来到海南,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北归离开海南。他在海南度过了三年时光。春节是我国民俗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欢庆、灯火、祝福连成一片。九百多年前的东坡,如何在海南儋州度过这三年的上元节呢?
锦绣交辉上元节
“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
东坡一生好诗词,但是他没有以“春节”为名创作过诗词。虽然春节民俗源远流长,但古时春节指代的时间与现在不同,春节最初指立春或春季。
东坡诗歌《新年五首》令人触景生情,其中一首写道:“晓雨暗人日,春愁连上元。水生挑菜渚,烟湿落梅村。小市人归尽,孤舟鹤踏翻。犹堪慰寂寞,渔火乱黄昏。”这首诗写于惠州,诉说新年寂寞,其他四首的内容和风格也是如此。诗中提到的“人日”指正月初七,相传是人的诞辰日;“上元”是正月十五,即元宵节,又称上元节。诗里没有提到的正月初一为“元日”,又称“元日节”。在这三个节日中,古人通常过的是“元日节”和上元节。

明代朱之蕃临苏轼像轴局部。(故宫博物院藏)资料图
北宋王安石的《元日》说的就是“元日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正是过年景象,放爆竹、喝屠苏酒、新桃换旧符都是过年的重要习俗。那时的“元日”,各地张灯结彩,游戏宴饮,把酒言欢。汴京(今开封)还有朝会,朝廷接受各方入朝恭贺。但宋代最热闹的节日不是“元日”,而是正月十五上元节。
宋代词人李清照在《永遇乐·落日熔金》里回忆往事道:“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词中,“三五”是“十五”的别样说法。在当年汴京的元宵节中,女孩戴着金银首饰盛妆过节。而此时的李清照已步入人生晚年,感叹自己如今憔悴,“风鬟霜鬓”,不好意思与人共度元宵,夜间只能待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稍早于李清照的柳永在《迎新春·嶰管变青律》一词里说元宵节:“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柳永是词人,他以文学的手法描述了汴京元宵节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各式彩灯仿佛绛树(即珊瑚树)正燃、“鳌山”(即彩灯制作的假山)高耸,可见当时景象的壮观。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他早年在汴京的见闻,其中专门说到元宵节。当天,汴京宣德楼前的御街上,到处都是灯山上彩、锦绣交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的盛况。
第一个上元节
“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伊威”
东坡在儋州过了三个上元节,每个上元节都或有诗或有文记叙自己怎样过节。
元符元年(戊寅年,1098年)上元节,是东坡居儋的第一个新年。他写了《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使君置酒莫相违,守舍何妨独掩扉。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伊威。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诗题“过赴儋守召”中,“过”指他的幼子苏过,“儋守”指儋州军使张中。东坡携苏过居儋,初得张中帮助,住在儋州伦江驿。这首诗应是他住在伦江驿时写的,其后又有《新居》诗记录在儋州城南自建新居事。
张中置酒请苏过共饮,因为张中好棋而苏过能棋。东坡不会下棋,曾在《观棋》诗序里说自己不懂下棋,曾在古松流水之间听到棋声,欣然而喜,顿生学棋之意,终不能会,只能做一个安静而不知疲倦的观棋者。这个上元节晚上,苏过不在家,东坡掩门守舍,与月光下的蜥蜴、风幔里的伊威相伴。在香烟袅袅中,他仿佛进入梦境,想到已不在人世的妻子、苏过的母亲王闰之。
诗中所说的“传柑”指的是元祐八年(1093年)的事。东坡任哲宗侍读时,在宣德楼上亲历了汴京的元宵节。他写下《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其二说“薄雪初消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回到家里,妻子王闰之还守着一盏残灯,东坡把侍饮所得的“传柑”送给妻子。东坡说得很平淡,却蕴有爱妻的一片深情。
第二个上元节
良月嘉夜,“放杖而笑,孰为得失”
东坡居儋第二年即元符二年(己卯年,1099年)的上元节就不一样了。在儋州过第一个上元节时,东坡居儋只有半年,人地生疏,艰难孤寂。
元符二年,挂着“琼州别驾”虚衔的东坡,像当地百姓一样生活。他给雷州知州张逢写信说:“新酿四壶,开尝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风。”虽然他举杯属影,暗示自己因张逢不在身边而感到孤独,但心情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这种变化从他的《书上元夜游》中也可以看出来。
元符二年上元节晚上,几个儋州老书生来看望东坡,并对他说:“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东坡欣然从之,和他们一道逛儋州夜市:“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这当然不同于汴京上元节之夜,但这一夜却让东坡有别样的感受。
一地有一地的风情,东坡在密州过上元节时,填了一首《蝶恋花·密州上元》,说到杭州的上元节场景:“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也说到密州的上元节场景:“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这些都和儋州的上元节场景不同。他在逛夜市时享受到独有的快乐,回家时已是三更,不禁“放杖而笑”,感叹“孰为得失”?是呀,东坡流贬儋州,很多人认为是“失”;但在其他地方都得不到的儋州之乐为他享有,难道不是“得”吗?

《东坡博古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苏东坡与友人聚会鉴赏古物的场景。资料图
第三个上元节
“追和戊寅岁上元”
元符三年(庚辰年,1100年)上元节,东坡写了《追和戊寅岁上元》一诗。在这之前,天门冬酒酿好了,东坡一边过滤一边品尝,不觉大醉,事后写诗《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载酒无人过子云,年来佳酝有奇芬。醉乡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诉说饮酒之醉,并从中感受新年的快乐。
东坡在《追和戊寅岁上元》中写道:“春鸿社燕巧相违,白鹤峰头白板扉。石建方欣洗腧厕,姜庞不解叹蟏蝛。一龛京口嗟春梦,万炬钱塘忆夜归。合浦买珠无复有,当年笑我泣牛衣。”这首诗“追和”其居儋首个上元节时写的《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
苏过随侍父亲在海南,妻儿都留在惠州。东坡诗以“春鸿社燕巧相违”喻苏过和妻子的分离,以白鹤峰住地木门未经雕饰喻她们生活之贫寒,又用西汉石建孝父的故事形容苏过纯孝,用东汉姜庞孝母的故事形容苏过之妻纯孝。随后,他又回忆起自己和妻子王闰之在京口(今镇江)和钱塘(今杭州)的生活,恍如梦境。这首诗多用典,借此告诉人们他在这个上元节联翩忆想,正应了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里所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
东坡居儋三年的上元节就是这样度过的。其中,第一个上元节时的孤寂,是他从惠州到儋州的过渡;第二个和第三个上元节时,他或与儋州百姓同乐,或自得其乐,悠然沉浸其中,俨然已是儋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