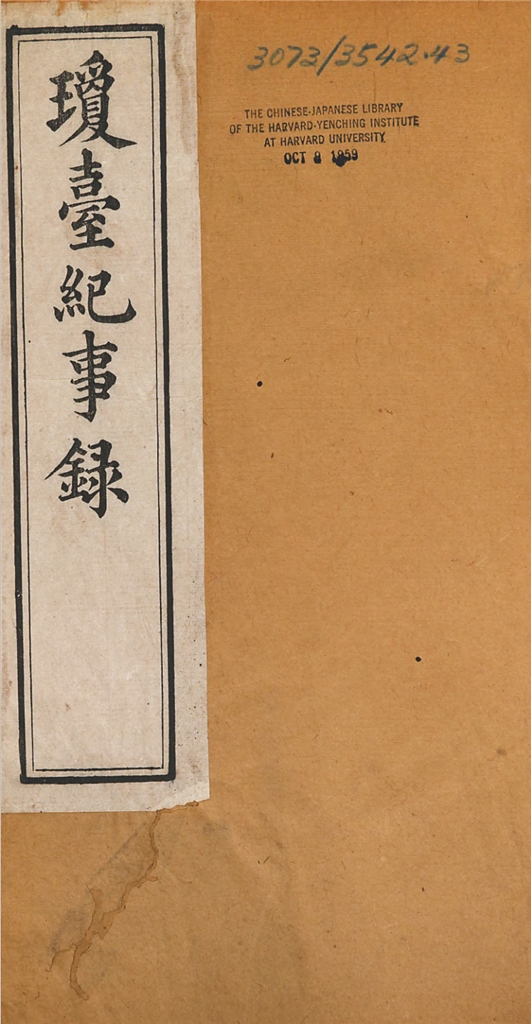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历代对陶渊明诗歌价值和地位的发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从“和陶诗”的出现和发展可以窥见其历史脉络——归功于苏轼,肇始于北宋,元代仍流行,明清达巅峰。

苏东坡在儋州三年间写下了大量“和陶诗”。图为纪念苏轼的儋州中和东坡书院。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元才摄
从东晋到南北朝,陶渊明主要作为隐士被接受。
到了隋唐五代,文人们尊崇陶渊明的主要缘由仍然集中在其人格操守和人生选择上,韦应物等人在陶诗的基础上发展了唐代山水田园诗,陶诗的艺术特征和价值开始被重视。陶渊明作为诗人的身份,到了北宋时期才被真正的“发现”。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及至明清两代,则是“和陶诗”创作的高峰时期。
“和陶诗”创制者——苏东坡
“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
北宋人发现了陶诗的意境、理趣和诗风。当然,这当中对陶诗发掘与接受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就是苏轼,他说:“始吾于诗人,吾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李泽厚先生指出陶诗“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苏轼不仅推崇陶诗,还亲自创作了109首“和陶诗”,这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瞩目的。
“和陶诗”是指用次韵的形式,追和陶渊明原诗而创作的作品,遵循陶渊明原诗的韵脚而依次用韵。在苏轼之前,和韵诗一般用于同一时代文人之间的酬答,几乎没有人运用和韵诗追和古人,苏轼对于以和韵诗追和古人的这种文学现象来说,是首创者。
苏轼在给其弟苏辙的信中曾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苏轼的“和陶诗”是其在政治失意、处境窘迫的情况之下应运而生的。尽管苏轼从未像陶渊明那般决意归隐,事实上苏轼也没有一刻脱离浑浊的官场。然而他却在闹市之中搭起了“隐居躬耕”的舞台,演绎并深深地进入陶渊明这个角色。
创作于扬州、惠州、儋州
“陶诗淳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
苏轼的“和陶诗”大多作于晚年,创作地点主要集中在扬州、惠州和儋州。
《和陶饮酒诗二十首》是苏轼和陶之始,作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时年五十七岁,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诗中描述诗人酒后的感怀,表达苏轼对陶渊明的仰慕,也抒发诗人得酒中真趣之后的感悟,如和诗一“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说诗人自己被尘世间的繁杂事所缠累,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局;和诗十三“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诗人说醉中虽然可乐,但仍然没有进入不生不灭的境界,随即发问怎样能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不醉不醒之中呢?可见此时诗人虽心中向往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但一时难以摆脱尘网,只能暂时饮酒自娱,以不醉不醒处世。苏轼此时的诗境与陶诗归依田园的宁静和恬淡毕竟不同。
《和归园田居六首》是苏轼惠州和陶的首篇,作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是苏轼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的第二年。组诗序言这一年三月四日,苏轼游览白水山佛迹岩,悠然自得,好不畅快。夕阳西下之时,诗人归途经过水北荔枝浦,还与一位八十五岁的父老相约荔枝成熟之时,再携酒来游。归家后一觉醒来听见儿子诵陶渊明《归园田居》,有所感怀,于是创作了组诗,寄给自己的莫逆之交参寥。《王直方诗话》中评论说:“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田园六首》,乃与渊明无异”,可见惠州时期的“和陶诗”与扬州时期在风格上有所区别,惠州“和陶诗”与陶诗的风格和内涵更加接近。
然而,组诗虽题为《和归园田居》,却并无田园气息。此时的苏轼对自己的宦海经历,已经从孤标傲世向超旷坦然过渡,表达了饱经忧患的宁静致远。在惠州期间,苏轼还创作了不少和陶诗,如《和陶咏贫士七首》,感叹岭海生活的贫苦;作《和陶时运》,抒发与家人团聚的欣喜;又借《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与陶渊明、葛洪在精神上同游同归,是苏轼和陶诗中比较具有哲思的一组作品。
儋州时期是苏轼“和陶诗”创作的高峰期,苏轼在那里创作的一百二十多首诗作中,“和陶诗”占有一半的分量。儋州三年,是苏轼贬谪生涯中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此时的苏轼在政治上仍无实权,但他深入百姓,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文学创作也达到全新境界。“和陶诗”是苏轼儋州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苏轼在海南的生活和思想。

苏轼约有一半的“和陶诗”是在海南儋州所作的。图为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吉林省博物院藏
苏轼每到一地都为民着想,绍圣四年(1097年)秋冬间,诗人远谪甫定,见儋州百姓忽视农业生产,生活水平低下,深感哀痛,因此创作了《和陶劝农》,呼吁改变儋州的落后局面。苏轼刚来到儋州时僦官屋数椽以居,绍圣五年(1098年)董必到广西查访,派人过海查看苏轼的近况,发现苏轼住在官舍中,遂下令将其赶出。苏轼便在城南污池之侧买下一块空地以搭建陋室,名之曰“桄榔庵”。苏轼《和陶酬刘柴桑》一诗中便记载了当地居民,帮助他盖房子。诗中说:“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处,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可见诗人处穷而乐,随缘自适。这一时期,苏轼在饮食生活方面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中写苏轼年逾六十而亲自治理园圃,诗人将自己比喻为“蓬头三獠奴”,他细心观察物象,从早韭、晚菘的生长中,悟出了“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和陶下潠田舍获》写苏轼在居所积肥凿泉,雨后看见菘莱发出新芽,树上长出木耳,但因它们还小,不忍烹煮,只能绕着它们徘徊。又自嘲说“齿根日浮动”,不宜吃肉,索性招呼儿子拆掉鸡窝。比起陶渊明原诗更加质朴超脱,更多地表现了苏轼的旷达诙谐。正如南宋舒岳祥在《阆风集》中所说:“东坡苏氏和陶而不学陶,乃真陶也。”苏轼将流放儋州当作是一种退隐,积极地融入这片土地。《和陶酬刘柴桑》写苏轼在儋州栽培薯芋,认为给皇帝进贡的淇上白玉延山药,也比不上海南的薯芋,诗中结尾说“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说明苏轼在海南已有归宿感。
苏轼和陶渊明都胸怀高远,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能将儒家的经世济民与道家的淡泊自然相结合。苏轼任扬州知州始和陶诗,藉陶渊明的安贫乐道,浇宦海不平之块垒;被贬岭南,苦中作乐,越发能在精神上与陶渊明契合,他遍和陶诗,书写自己对生命的反思。两个高贵的灵魂之间跨越时空而共鸣。苏轼的和陶诗在于化解生活中的种种苦闷,有的则表现他历尽沧桑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言:“陶诗淳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和陶之诗代不乏人
“和凑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
苏轼“和陶诗”甫一诞生,就引起了文人们的追随,其弟苏辙就有和陶之作,存世的“和陶诗”有四十多首,然而与陶诗和苏轼“和陶诗”相比,苏辙的“和陶诗”议论说理的成分更多,而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推敲上则不及前二者。
苏门学士亦各有继和之作,如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这些诗人的“和陶诗”虽名为和陶,实则是出于对苏轼的追随。所以,他们的作品中虽有陶渊明的恬淡自然,更多的是苏轼之气格。
及至南宋,“和陶”现象蔚然成风,主要有李纲、吴芾、陈造、张拭、于石、释觉范、张锐等。宋人王质《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小序中评价宋代人的“和陶诗”说:“闲居无以自娱,随意属辞,姑陶写而已,非自附诸公也。”可见宋人继踵苏轼而作的和陶诗多有附庸风雅之意,精品不多。
金元时期,追和陶诗的风气仍旧继续。金代后期的文坛领袖赵秉文,共留下35首“和陶诗”。元代和陶风气依旧流行,这与元朝统治阶层轻视科举制度等政治背景有关。元代儒学倡导者的郝经为议和而入宋,被南宋朝廷所滞留,在这期间创作了118首“和陶诗”;被元世祖忽必烈评为“不召之臣”的刘因,则写有76首“和陶诗”。此外,方回、戴表元、张养浩等人,皆有和陶诗作。
明代的李贤和周履靖二人,可以说是“尽和陶诗”。李贤《古攘集》共收录125首的“和陶诗”,除《形影神三首》外,对余下所有陶诗都进行了次韵;周履靖在《五柳赓歌》中,共辑录了自己创作的127首“和陶诗”。二人的创作被视为明代“和陶诗”创作的高潮。
清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有追和陶诗的作品,如查慎行、舒梦兰、姚椿等。从陶渊明所写题材来看,以《饮酒》为例,就有施闰章《客中独酌偶和陶公饮酒》二十首、沈栻《和陶诗饮》、方以智《和陶饮酒》等。清朝乾隆皇帝也有和陶之作——《和陶二首用其韵兼效其体》,可见“和陶”之风在清代的盛行。
朱熹曾如此评价苏轼“和陶诗”:“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东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和凑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且不论朱熹的评价是否允当,却说出了和韵这种创作形式的束缚,使得大多数和陶诗形似而神离,存韵而损意,这恐怕是后世“和陶诗”的普遍为问题。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