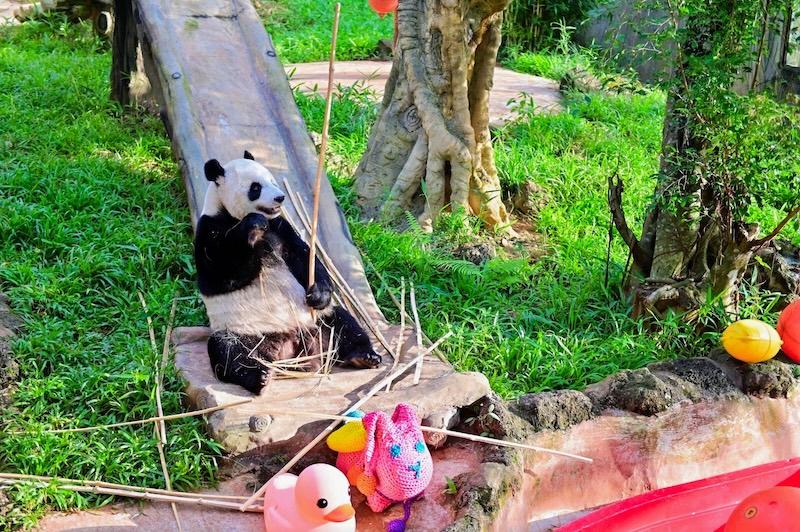烟波浩渺的大洋之上,一叶叶商船载着奇珍异宝穿梭于东西海域,其中一缕沉香气息,贯穿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脉络。
发轫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的流通之道,更因香药的大宗贸易而孕育出一条馥郁芬芳的“香路”。与瓷路、茶路几乎都以中国为始发港不同,香路多以中国为抵达港,有时也以中国为始发港。
沉香,是这条海上香路的代表香料。上千年间,既有域外奇香飘入华夏的温润,亦有中华香韵远播异域的绵长,成为古代中外文明双向互鉴的生动注脚。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场景。手绘/陈海冰
海上香舶来
1973年,泉州湾后渚港的滩涂中,一艘南宋古船的残骸破土而出,为千年海上香路揭开了鲜活的面纱。
次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这艘残长24.2米、宽9.15米的古船尽显匠心——13个水密隔舱的精巧结构,留存完好的桅座与龙骨,印证着宋代造船术的精湛。正是因为造船技术的发展,才为沉香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基础条件。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艘沉船的船舱中仅未脱水的香料便重达2300多千克,其中自然少不了沉香。经考证,这艘载重近200吨的中型远洋货船,从东南亚满载香药归航,在南宋末年的风浪中沉睡于此,成为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实物佐证,更让“海上香舶来”的历史场景跃然眼前。
沉香传入华夏的历史,远比这艘古船更为久远。“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的这句诗,提到了唐代以沉香木雕刻而成的沉香亭。早在唐代,沉香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货物。《旧唐书》记载,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
不知这沉香亭的材料是走陆路还是海路到的长安。但唐代时南海交通已初具规模,隋唐一统后,以广州为起点,通往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及东非等地的远洋航线“广州通海夷道”逐渐形成,让波斯湾与南海的贸易动脉彻底贯通。
当时,阿拉伯地区的商船载着域外奇珍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广州港靠岸,东南亚地区的沉香便随着这股贸易浪潮,走进宫廷府邸与寻常巷陌。
到了宋代,海外贸易蓬勃发展,香料是最重要的舶货之一,甚至出现了专门贩运香料的大型贸易船“香舶”。南宋《诸蕃志》详细记载了当时58个海外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大多与中国有着经贸往来,向中国输入沉香等为代表的香料。
“炎区万国侈奇香,稇载归来有巨航。”这两句出自宋人洪适所作的《沉香浦》。所谓沉香浦又名贪泉,王勃《滕王阁序》中有“酌贪泉而觉爽”之句。沉香浦位于今广州城郊,因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曾投沉香于其中而得名。而洪适的这两句诗,点出了沉香是古代广州的大宗进口商品,“载”“巨航”之词,可见其数量之多。
宋代的沉香贸易呈现出多元格局:既有蕃商冒充贡使带来的“贡品”——占城使团曾以象牙、沉香为礼,换得宋朝近千匹丝织品的丰厚回赐;亦有民间商船的常态化贩运,苏门答腊的沉香经泉州、广州登陆,再分销至各地。北宋雍熙四年(987年),朝廷还派专使前往东南亚招揽商人、购买香料。
宋人对沉香的品鉴也日益精细,“真腊为上,占城次之”的等级划分,“结皮十分即为沉香”的标准界定,折射出全民用香之风的炽盛。
到了明清时期,沉香贸易虽受海禁影响,却在曲折中延续。明末澳门也成为新的沉香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地,葡商驾着商船穿梭于南洋与中国之间,汤显祖“采香长傍九洲山”的诗句,正是这一场景的生动写照。
这一时期,从东南亚到阿拉伯半岛的商队,仍执着地将沉香运往中国,而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也推动着香药产地的资源开发与品类细化,让这条海上香路始终未曾中断。
香渡重洋去
当域外香料源源不断涌入中国时,中华大地上的香药也循着海上丝路扬帆远航,形成“香渡重洋去”的双向流通格局。
沉香、麝香、樟脑等为代表的香药因体积小、价值高、用途广,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理想商品,通过朝贡贸易、民间贩运、僧人往来等多重渠道,从我国辐射至东亚、南亚乃至非洲、欧洲,成为文明交流的芬芳使者。
古代,东亚是中国香药输出的核心区域,“东海航线”上的商船承载着沉香与情谊,频繁往返于中、朝、日之间。以沉香为代表的香药常作为国礼传递善意:永乐元年,朝鲜太子为父治病,遣使携布匹求购龙脑、沉香等药材,明成祖不仅命太医院悉数赏赐,更归还布匹以示体恤;宋隆兴元年,孝宗遣徐德荣赴高丽,以沉香为核心的珍玩厚礼,彰显着两国的睦邻友好。
民间贸易往来更是如火如荼。唐代,日本商人八郎真人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新猿乐记》记载其贩运的“唐物”中,沉香、麝香等香药琳琅满目;北宋福州商人周文裔赴日时,送给一位当地官员的礼物就有百两沉香、五十两丁香。北宋时,福州虞瑄、广南陈文遂等商人相继赴朝献香药,让沉香的香气弥漫在朝鲜半岛的宫廷与市井。这些都是沉香在中外民间贸易的缩影。
说到携带沉香奔波在海上丝路的著名人物,不得不提到唐代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出发准备的物品中,沉香等香药是重要的一项。相传扬州香药市场十分兴隆,鉴真曾在扬州采购麝香、沉香等。
南亚作为中西交流的枢纽,既是中国香药的目的地,更是中转集散地。沉香、桂皮、大黄等香药经海上丝路抵达印度、斯里兰卡后,一部分满足本地需求,一部分由南亚商人转销至伊朗、阿拉伯地区。
9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操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斯拉夫语的商人经陆路和海路,从东方行至西方,又从西方行至东方……他们从中国携带着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其他各地的商货返回红海,再将货物运至凡莱玛,再航行于西海中。”
这种中转贸易不仅扩大了中国香药的影响,更让沉香成为连接东亚与西亚的贸易纽带,在不同文明中留下印记。
以沉香为代表的中国香药通过海上航线运往他国,不仅改变了域外的用香习惯,更推动了当地香药文化的发展。如日本,沉香融入茶道、花道等传统礼仪;在东南亚,沉香与本土宗教仪式结合,形成独特的香文化;在西亚与非洲,沉香成为医药、香料产业的重要原料。
这种文化融合与互鉴,让沉香超越了商品的属性,成为海上丝路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节点海南岛
在波澜壮阔的海上香路中,海南岛以“出产上乘沉香”与“贸易中转站”的双重身份,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这座孤悬南海的岛屿,北望雷州半岛,南接东南亚,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既能孕育优质沉香,又能承接东西往来的商船,让海南沉香的香气飘向全球。
北宋初年,就已有很多往来东南亚与广州的商船停泊在海南岛避风和补给。《咸淳临安志》记载:“广南西路有大舶困风于远海,食匮资竭,久不能进,告穷于则,则命琼州出公帑钱三百万以贷之。”当时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只要有船遇台风,海南不仅让它进港避风,还拿出公共经费借给船商让其渡过难关。
由此,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因为这特殊的地理区位,海南岛上的沉香和其他土产也随着这些商船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苏东坡就曾记述当时海南民众“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的状况。
当时,福建、浙江等地商人每年冬季来海南岛收购沉香等香料。南宋绍兴年间,广州、泉州、明州三路市舶司所购的香料中已列出了“海南苏木、熟速香”。这一过程中,海南岛的香料不但销于国内各地,而且也逐渐被其他国家的商人所重视。
被贬海南的北宋宰相丁谓,在其所撰写的《天香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曾有大食(今阿拉伯地区)货船停靠海南,其中为首的商人整日大摆筵宴,但海南当地人却发现他们所焚的沉香“蓊郁不举、干而轻、瘠而焦”。于是,当地人找来海南沉香焚烧,让大食商人们认识了“如练凝漆,芳馨之气,持久益佳”的海南沉香。
这段故事不仅凸显了海南沉香的上乘品质,更说明其已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海南沉香的品类丰富,与域外沉香相得益彰,共同丰富着中外香药市场的选择。
明清时期,即便海禁森严,海南的沉香贸易仍韧性生长。明代丘濬“珍货来番舶”的诗句,描绘了外国商船载着货物赴琼贸易的场景。小叶田淳所著《海南岛史》记载,康熙二十六年至四十六年间,至少14艘商船往返于海南与日本之间,以沉香为代表的土产在日本备受青睐。
《华夷变态》中记录的浙江商人朱仲杨,便是当时民间贸易的典型代表。他定居琼州后,于康熙二十年装载沉香等土产东渡日本,虽历经一次失败仍坚持不懈,最终抵达长崎,这也印证了海南沉香在日本的吸引力。
海南既是沉香产地,又是中转枢纽,东南亚的沉香经此运往中原,海南本土的沉香也直抵日韩与东南亚,形成“双向流通”的贸易格局。从汉代开始,这种“中转+出产”的模式便已形成,历经千年而不衰,让海南在海上香路中始终占据特殊地位。
千年潮起潮落,商船往来不息,沉香的香气早已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肌理。如今,当“一带一路”的倡议再度激活古老的贸易通道,沉香的芬芳依旧在诉说着东西方交流的千年故事,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见证着文明的延续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