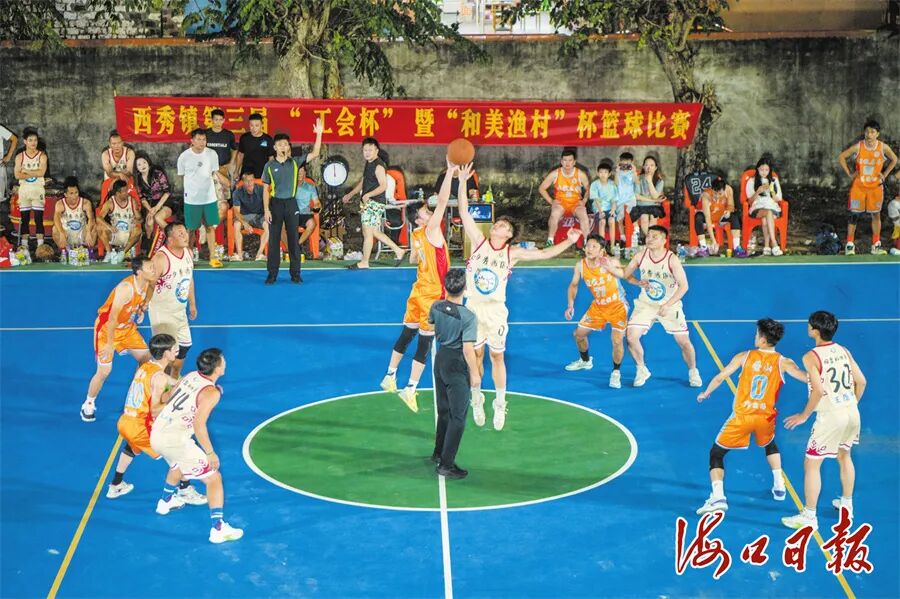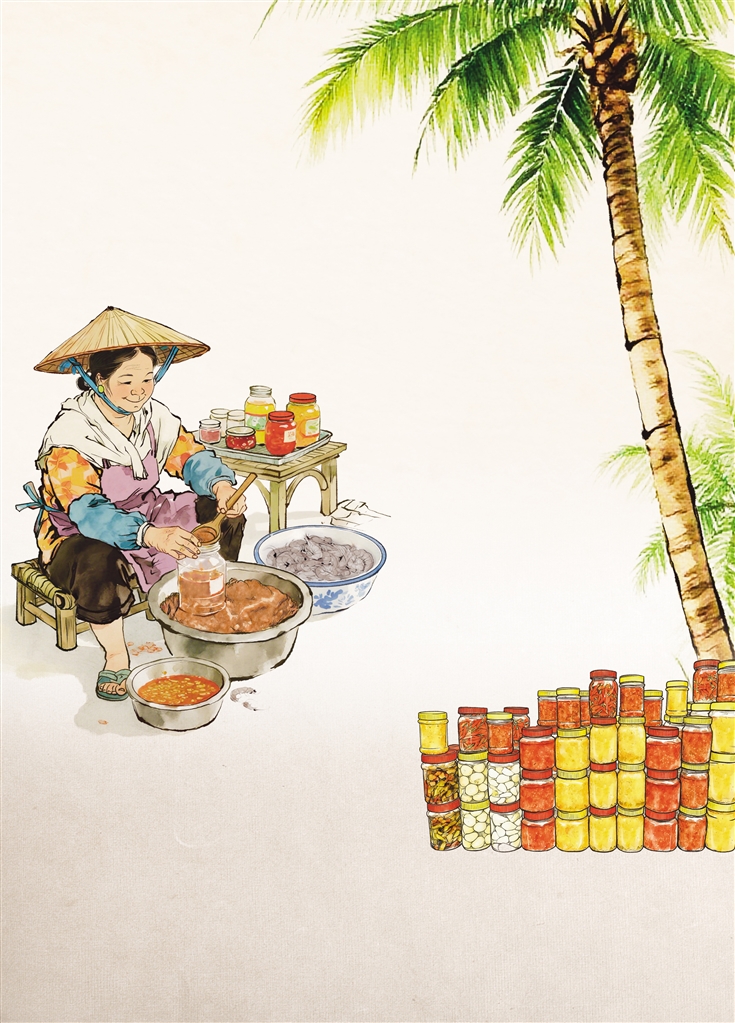■方波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重要时间体系,凝结了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与实践经验,其中大暑标志着夏季最为炽热的时期。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代表,瓷枕不仅承载着实用功能,更通过其材质选择、纹饰设计及使用习俗,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与文化心理。
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古代枕头的材质经历了从天然石材到木质、陶质,再到草质、玉质、瓷质、丝质、布质等材质的演变过程,其中瓷枕因质地坚硬、触感凉爽的特点,自唐宋以来便成为夏季寝具的优选。文献记载表明,古人不仅注重瓷枕的物理属性,更将其与健康养生观念相结合,认为使用瓷枕可“清神明目”,这种功能认知与大暑时节驱热避暑的生活需求形成了直接呼应。从文化交融的角度审视,大暑时节所代表的时令智慧与瓷枕工艺中蕴含的造物哲学,共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瓷枕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历程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关联。早期瓷枕的雏形可追溯至隋唐时期,最初多以冥器形式出现于墓葬中。这一时期的瓷枕形制相对简朴,以几何纹样和自然物象为装饰主题,工艺上则以三彩釉与绞胎技法最具代表性。三彩瓷枕通过黄、绿、白等釉色的交融形成色彩斑斓的效果,而绞胎工艺则通过不同色泥的揉搓、压制,形成类似木纹的肌理,两者共同构成了唐代制瓷业高度发达的艺术见证。随着唐宋之际丧葬观念的转变,瓷枕逐渐突破冥器功能的局限,开始进入世俗生活领域。
据宋代文献记载,瓷枕因具有“清凉去火”的实用特性,在夏季被广泛用作寝具,其硬度与透气性较之传统草枕更具优势,这也为后世“大暑伏天睡瓷枕”的民俗传统奠定了物质基础。

宋代磁州窑白釉褐彩腰圆枕。海南省博物馆藏
两宋时期,瓷枕的制作工艺与文化内涵均达到历史高峰。
窑口体系的完善推动了瓷枕生产的专业化,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名窑均以不同风格的瓷枕闻名。这一时期的瓷枕在造型设计上更加丰富,除常见的长方体形外,虎形枕、伏虎枕等仿生造型因契合民间信仰而广受欢迎。
在装饰艺术方面,釉色运用呈现多样化趋势,白釉划花、黑釉剔花、青釉刻花等技法竞相发展,其中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工艺尤为突出,其在白色化妆土上以笔绘就的水墨纹样,将书画艺术与实用器物完美融合。这一时期的瓷枕开始出现题写诗词的现象,枕面常见《诗经》选句、民谚俗语或吉祥祝词,这种“枕上诗”现象不仅是文人雅趣的延伸,更反映出器物承载文化信息功能的深化。
元代瓷枕继承了前代的装饰工艺,这一时期瓷枕装饰风格深受文人画风影响,枕面装饰转向对意境的营造,水墨山水、梅兰竹菊等文人画题材频繁出现。
明清时期,随着棉花普及与纺织技术革新,柔软舒适的布枕逐渐取代了瓷枕的日常实用地位,但瓷枕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的瓷枕制作转向艺术品和收藏品定位,景德镇窑的青花瓷枕、德化窑的象牙白瓷枕因追求极致的工艺品质而备受文人雅士青睐。清代还出现了镶嵌螺钿、彩绘珐琅的高档瓷枕,这些作品虽已脱离实用功能,却在装饰艺术层面延续了瓷枕的文化生命。

清代青花双狮戏球瓷枕。海南省博物馆藏
从隋唐冥器到宋元日用再到明清雅玩,瓷枕的演变轨迹不仅勾勒出中国古代手工艺的发展脉络,更折射出不同时代社会习俗、审美观念与技术进步的深层联动。
从社会功能看,瓷枕的文化象征具有阶层差异与时代变迁的特征。早期瓷枕纹饰多以简单几何图案为主,随着宋代市民文化兴起,装饰题材逐渐丰富,出现了包含戏曲场景、市井生活等世俗化元素的作品。元明清时期,瓷枕生产呈现明显的商品化趋势,其纹饰开始系统化运用吉祥图案,这种转变既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也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通过物质载体与精神追求的深度融合,瓷枕不仅成为解读传统生活美学的重要物证,更在特定节气语境下,构成了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对话的特殊场域。

宋代临汝窑青枕。上海博物馆藏
大暑时节与瓷枕文化的交融,是自然节律与人文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交融既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功能适配,又延伸到精神层面的审美表达,更渗透至社会层面的礼俗实践。当大暑的热浪如潮水般侵袭,古人却在枕席之间开辟出一方清凉的诗域。那方寸瓷枕承载着的,正是中华儿女在顺应季节流转中创造的生存美学与心灵慰藉。(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