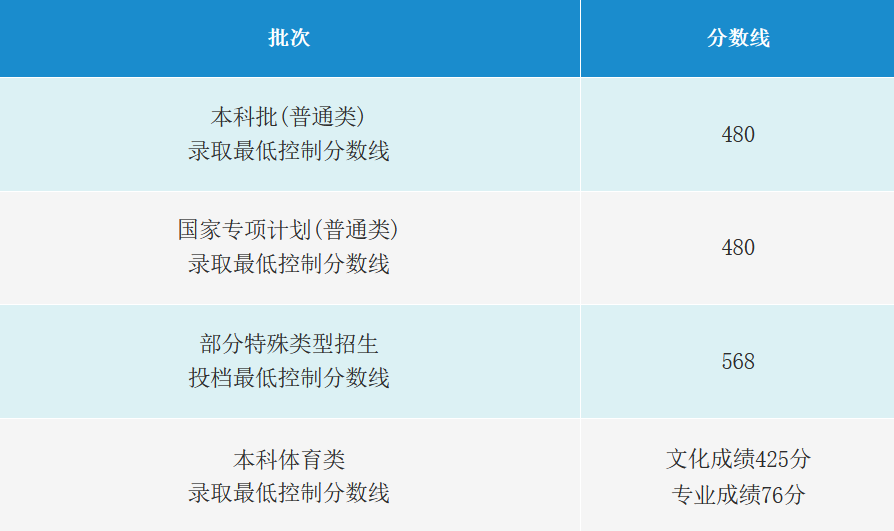临高文庙。张志海摄
汉会稽有“一钱太守”刘宠,清临高有“馈米县令”樊庶,都是为官清廉的典范。不过樊庶的事迹却鲜为人知,未免令人叹憾。
樊庶生长于富庶的扬州,工诗善画,与当时江南诸多名士都有交游。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樊庶被选派到偏远的海南临高担任县令,从此开始了他在临高为期十年的宦海生涯。在任期间,樊庶曾多次捐献俸禄修建县署、县学、城墙、路桥,又根据当地民情民俗劝农重商、施药济民、鼓励文教,使临高的面貌大为改观。后来,樊庶家财耗尽,陷入困顿。民众纷纷自发送米至县署,樊庶因此赢得“馈米县令”的美誉。
内除旧弊外防患
清代临高农业凋敝,鱼盐不兴。樊庶到任时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底,面临各种清账和催缴。樊庶让差役敞开大门,在广泛听取民众诉求后,很快总结出当地五大陈弊并逐一革除。樊庶此举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他们在三盈市立了一块“戴德碑”,以表达对樊庶革除旧弊的感恩之情。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早春,樊庶详细考察了临高的地形,发现临高海岸线长达百余里,元明时期堆筑的墩台早已坍塌,马袅、博顿两营兵力薄弱,存在严重的海防隐患。巡视时,他看到疍民生活艰辛,写下一首《巡抚海口记事》:
匹马频行历海滨,荒烟深处旧关津。
白波满目儋澄界,黄笠遮头疍灶人。
三尺矮檐防飓母,一拳小石祀龙神。
廿年兵燹奇荒后,纵有鱼盐不救贫。
诗中述及临高疍民的风俗。他们为了预防台风,建造低矮的房子;因为惧怕风浪,奉祀龙神祈求平安。
巡视之后,樊庶决定从马袅三家村到新盈博顿村近百里,每十里左右设置墩台一座,共设墩六座、台六座。十二座墩台组成一条警戒链,只要一处燃起烟火,其他墩台就可以相继点火报讯,顷刻间将消息传遍百余里。此外,樊庶还在博顿、乌石、新安、石牌等港增建炮台,并参考明代的民壮机兵制招募民兵,昼夜巡查,既省了增兵的军饷,也起到了防范的实效。
樊庶的功夫没有白费。当年十二月底,海贼作乱,沿崖州北上,逼近儋州,威胁临高。樊庶率所部团练营兵及皂快、家丁二百余名沿港口堵御。海贼见状不敢贸然进犯,临高得以安全无虞。至今,临高还残存着墩台的遗址。
捐资修建百废兴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秋之际,临高遭遇飓风。此次飓风破坏力很大,县城东门、西南门破损,城外文澜江上的临江桥垮塌,城内县署、文庙、城隍庙和大批民宅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灾后重建需要大量经费,然而当时临高府库空虚,若是向下摊派,无异于让受灾民众雪上加霜。为了减轻民众负担,樊庶决定自掏腰包,先后修复了城门、江桥和诸多坛庙。修临江桥时,樊庶采用“油灰法”,制造了古时的“混凝土”。具体做法是将石灰拌上桐油,再用水调和成胶泥,用来填塞孔隙、黏合土石、固定桥墩。次年,樊庶又用同样的方法,修复了西塘都的谭流桥、县城东的官荣桥。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樊庶开始着手修建县署、县学。这些工程耗时较久但意义重大。
县署是政教所在,贵在威仪,可使当地官民存敬畏心,也能令继任者生归属感。但临高县署由于沿海潮湿、台风屡至而破败不堪。樊庶在《重建临高县治记》中记载,他到任之时,县署“几无以避风雨”,此前的临高县令就任多不过五载、少不出数月就辞任北归,因此多将此地作为旅邸,无心经营。樊庶到任时,曾对县署进行简单修整。飓风过后,樊庶开始大规模重建县署。本次重建,樊庶仍是自掏腰包,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才修缮完毕。樊庶在新修的县署二堂内,先后完成了《苏文忠公海外集》和康熙《临高县志》等文集、志书的编纂,为临高乃至海南的文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图: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书影。

资料图:樊庶为《苏文忠公海外集》写序。
文庙是储才之地、文教中心。临高的文庙原称儒学,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明清时与文庙合二为一。因为选址濒临海滨,或遭兵燹,或遇台风,文庙屡修屡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樊庶开始着手重建文庙。本次工程颇为浩大,前后历时一年半,花费一千余两,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九月方才告竣。告竣之时,临近孔子诞辰,樊庶于当年八月二十七日主持祭孔典礼,引来诸多民众围观。学政翁嵩年为文庙撰写了碑记,盛赞樊庶重视文教,改善地方风气,使临高“穷海极壤,廪廪有邹鲁之风”。士民们为此合立“弦歌万户坊”,纪念文庙落成。
文庙落成后,樊庶亲自到讲堂为士人讲授课艺,还发布了《勉科举示》的公告,提出愿意典衣举债送士子去赶考,足见樊庶的励学之心。
除了鼓励文教外,樊庶还格外重视农商发展。当地集市市主收租时往往肆意抬价,商民敢怒不敢言。康熙《临高县志》记载:“康熙四十三年,知县樊庶捐俸悉买其地,听贾者建屋宇贸迁,商民称便,其市日盛。”为感激樊庶为商户买地立市,商人王昌绪等倡议在墟市入口立“两朝一人碑”,感念樊庶之举。
此外,樊庶还兴建义学,创建育婴堂,广谋药饵,遍施村落,捐浚甘泉,以资居民汲引,做了许多有利民生的实事。
“馈米县令”传美名
樊庶未到临高之前,过着富足闲适的生活,从他广交名士、雅好金石便可略窥一二。任职临高后,他独自出资修建文庙、衙署、城隍庙、天后宫等,仅文庙就用银一千余两,此外修路铺桥,建澹庵祠、正学讲堂、关帝庙又不知花费凡几。

资料图:樊庶编康熙《临高县志》书影。
康熙《临高县志》记载,县令每年俸禄不过四十五两,然而樊庶用于兴建的花费不下数千银两。贡生王伟业在《馈米亭记》一文中提到,樊庶因廉介,“几无以致薪米”。当地人得知樊庶困窘至几近断粮,到了秋收便纷纷自发给樊庶送米:“于是建亭于县治辟门东,届秋成,家携米各一升,致馈于亭”。馈米亭今日虽不存,但馈米的故事却收录于方志之中。
王伟业认为,众人给樊庶馈米之事与“一钱太守”刘宠的典故同为佳话。东汉刘宠任会稽太守,因为清廉广得民心。他调任入京时,山阴县父老各备百钱相送,刘宠推脱不过,只得收下每人一钱,以示谢意,从此青史留名。樊庶在临高“兴利如雨之润草木,剔弊如火之燎野草”,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民众用馈米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所谓“夫升米不及百钱,公之治临,远过刘之刺会;吾民酬此,其负愧于山阴父老云多矣”。临高父老送给樊庶的一升米不到百钱,比不上会稽父老回馈给刘宠的,但樊庶为临高作出的贡献,比起刘宠对会稽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是清廉爱民的佳话,“一钱太守”天下闻名,“馈米县令”却鲜为人知。但历史没有遗忘,樊庶的功绩得到了后世的认可,道光《广东通志》评价樊庶:“清廉明洁,百废俱举,实惠及民,为近日循良之首。”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